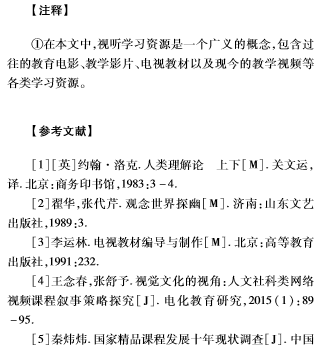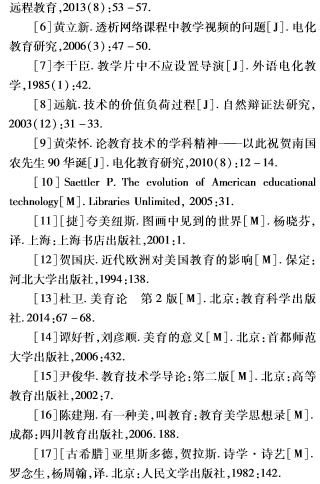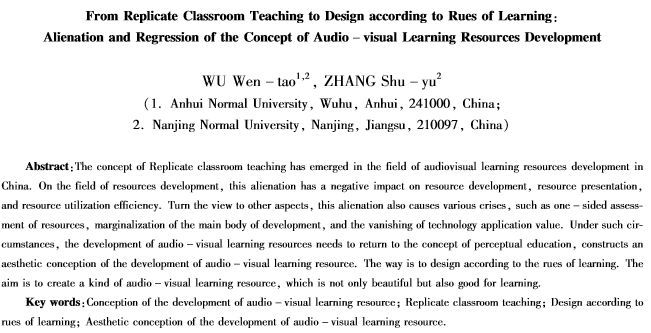从复制主义到寓学于美: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观的异化与回归
| 全文共8834字,建议阅读时9分钟 |
本文由《现代远距离教育》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吴文涛、张舒予
摘要
我国视听学习资源开发领域显现出一种复制主义的观念异化倾向,这种异化对资源开发过程、资源呈现方式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同时,这种异化还引发了资源评价的片面化、开发主体的边缘化、技术价值的消解等深层次危机。因此,有必要反思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观,将其回归至肇始之初的感性教育理念。提出建构“寓学于美”的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通过实施“寓学于美”的资源开发途径,实现创制具有“学美与共”属性的视听学习资源。
关键词: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观;复制主义;寓学于美;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Locke)曾说:“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依据被他视为行动原因的观念。……其实,人的精神中的观念和意象才是不断地控制他们的看不见的力量。人们普遍地顺从于这种力量。”[1]受此启发,笔者结合自己的体验开始反思:在视听学习资源①开发领域,是否也存在一种控制着人们行动的力量———此力量成为一种指引着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的实践观念而被教育技术人“普遍地顺从”?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追问:隐藏在当下视听学习资源开发实践背后的这种观念是什么?在它的“控制”下,我们的实践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有问题,可否建构一种更好的观念从而指引实践走向更加理想的状态?为此,笔者通过一种观念的探索,进而揭示隐藏在视听学习资源开发实践活动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力量”,并由此进而努力建构一种新的观念。
一、复制主义: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观的异化倾向
若要进行这样一种探索,首先需要对观念这一概念有一个前提性的认知。观念是什么?这常常是一个哲学层面的抽象追问。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试图去解答这一追问。在柏拉图那里,观念以“理式”的形态出现;在康德那里,观念又演变为“先验”;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观念的代名词;在马克思那里,观念等同于“意识”……直至现今,哲人们还在前赴后继,继续追问着“观念”的本质。在本文中,“所谓观念,它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关于某一对象的相对定型化的映像、理解或文化观点。”[2]
在这一界定中,有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即“文化背景”、“某一对象”和“相对定型化”。首先,观念是依赖“文化背景”的,因而它会随着“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其次,观念是依附“某一对象”的,因而它会随着对象的改变而改变;第三,观念是“相对定型化”的,它通常指向多数人的共性观点,而不是少数人的个性看法。也就是说,假如“文化背景”与“某一对象”确定,那么观念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由上,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论的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观,是指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与“国内”这个文化下,业界多数人对于“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这一具有实践属性的对象的共性的认识或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反思:时至今日,国内业界在“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这件事情上究竟持有怎样的共性认识?显然,这一问题很难有具体明晰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下的实践中发现问题的些许端倪。
站在观念的层面反思今天国内视听学习资源开发实践的种种病症,笔者以为,其背后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复制主义的异化倾向。具体而言,它表现为这样一种复制主义的资源开发观:在开发者们看来,视听学习资源开发不是基于教育世界的一种创作设计,而是对教育世界(以传统课堂为主)的机械复制。就资源开发本身而言,这种观念至少已经导致以下三个具有逻辑延续关系的负面影响。
(一)稍显机械的资源开发过程
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在当下的各大互联网教育平台中,绝大多数视听学习资源都属于“课堂搬家”型资源。不管是过往的网络教育课程开发,还是今天的MOOC教学视频制作,多数情况下,人们实际上只是利用视听技术复制传统的课堂。如此情形下,开发视听学习资源几乎等同于对传统课堂的“实况录像”。
于是,视听学习资源的整个开发过程也演变成一种稍显机械的技术劳动。依据过往经验,摄制视听学习资源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创制过程,需要涉及用光造型、摄像构图、特技造型、动画造型、编辑配音等再创作环节[3]。然而,令人吊诡的是,时下人们的开发过程却极其简单,常常只需完成两个环节便完成一段视听学习资源的制作:首先,在传统课堂中架设一台或几台摄像机;其次,利用编辑软件对摄制的素材进行简单地形式处理与格式转换。且不说要进行上述复杂繁复的再创作环节,就连最简单的移动式拍摄、蒙太奇式编辑等操作手法都几乎很难在当前的资源开发中运用。概言之,在与过往实践比较的意义上看,当今的视听学习资源开发过程的这种机械性主要体现为:人为的再创作手段越来越少,对摄像机器、编辑软件等设备的依赖愈发严重。
(二)过于单调的资源呈现方式
这是机械的资源开发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视听学习资源开发已经沦为对传统课堂的“实况录像”,因而开发者便无需再对学习资源的画面、声音以及结构有太多的设计与处理。其结果便是,在当下的视听学习资源中,画面常常还是传统课堂的画面,声音每每还是传统课堂的声音,结构往往还是传统课堂的结构。
如此一来,视听学习资源的呈现方式自然显得非常单调了。假如将视听学习资源看作是一个视觉影像叙事作品,这种单调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叙事视角的单调,主要以教师为中心。在绝大多数的资源呈现方式中,教师无疑担当绝对的主角,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向学生灌输知识。第二,叙事结构的单调,过于平铺直叙。由于当前的视听学习资源过度强化教育功能,因而导致其一味采取线性的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变化较少,几乎不会出现平行蒙太奇、跳跃蒙太奇等影像叙事方式。第三,叙事时空的单调,过于依赖传统场景。如前所述,当前视听学习资源绝大多数都属于“课堂搬家”型资源,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拍摄场景单一,过于依赖传统课堂、报告厅等场景,忽视了创造性地开发传统课堂之外的广阔时空[4]。
(三)相对低下的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利用率低是单调的资源呈现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一旦作为观众的学习者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视听学习资源中所呈现的还是教师的知识灌输、线性的叙事结构、传统的时空场景,较少或不愿使用资源自然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常态已经被大量经验事实反复证明。仅以面向大学的视听学习资源为例,2003年以来,教育部组织各高校建设了数千门以“课堂搬家”型教学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的国家精品课程。有调查显示,在国家精品课程的应用方面,66.67%的被调查者所在高校很少使用其他高校相关学科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只有19.44%的高校在教学当中经常使用其他高校的精品课程,另有13.89%的高校根本不使用精品课程。此外,大部分精品课程参与者(85%以上)自身也认为精品课程对高等院校的教学影响不大[5]。也就是说,不仅是视听学习资源面向的应用者,就连视听学习资源的开发者自身,都承认资源的实际可用性不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课堂搬家”型资源本身单调的呈现方式的确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6]。
二、复制主义开发观引发的深层次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复制主义资源开发观业已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危机。就现状而言,这种深层次危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片面的评价方式
首先引发的危机便是资源评价方式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任何的考核评价均需以符合事实为根本依据。换言之,对实践的评价方式需根据实践的具体事实来选择。当开发视听学习资源等同于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实况录像”时,资源开发者的工作事实便是对资源的各种技术属性进行设置与编辑。如此一来,以技术属性为主的考核方式便成为一种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评价途径。
事实也正是这样。2013年,教育部发布了《精品视频公开课拍摄制作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无论是从名称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标准》明确指出,它“主要包括视频公开课的音视听录制、后期制作和文件交付等基本技术规范”),《标准》仅仅是一套规定精品视频公开课视频参数的技术指标。然而,鉴于精品视频公开课在我国视听学习资源范畴中的较高地位,《标准》一经发布,不仅成为视频学习资源开发主体的操作依据,也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考核视频学习资源的评价标准。于是,教育行政部门对于视听学习资源的考核评价,仅仅在技术指标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此时,相信对电视教材审核原则稍有知晓的同仁们便能发现潜在的问题,根据过往经验,针对视听学习资源的评价包括五个方面,即教育性、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和技术性[7]。因而,假如只对视听学习资源的技术性提出要求,而不对其其他维度的品质进行明确规定,便极易引发一种唯技术指标的片面评价方式。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资源开发实践变成一种机械的技术复制时,唯技术指标的评价方式不仅不能成为发现问题的监督工具,相反,它却在纵容实践问题的持续恶化。最终,在“机械的复制—片面的评价”的恶性循环中,对视听学习资源的考核评价便仅剩“技术标准”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二)边缘的开发主体
开发主体地位的不断边缘化是复制主义资源开发观引发的又一危机。大量的事实一再表明,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都存在大量从事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的教育技术工作者曾经或正在遭遇着边缘化的境遇。在视听资源开发的舞台上,教育技术工作者常常只能扮演着配角:他们按照外在的要求拍摄、按照技术的流程操作、按照规定的参数编辑。
更可悲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配角,如今都已经渐渐地被取代。时至今日,随着MOOC的风靡、微课的火爆,教育领域对视听学习资源需求愈发强烈。进而,在充足教育经费的支持下,从事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专业视频制作公司所替代,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当教育技术工作者秉持着复制主义的观念开发资源时,他们实际已经不是一类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人,而只是一类从事技术劳动的技术人。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仅仅作为技术人而存在的资源开发主体自然在教育领域毫无地位可言。更夸张一点说,即便不是被更具技术水平的其他群体所替代,仅仅从事技术劳动的资源开发主体未来也会被更具技术功能的智能机器所替代。
(三)消解的技术价值
视听技术在教育领域价值的消解,是迄今为止复制主义资源开发观所引发的最为严重、也是最需警惕的深层危机。具体而言,它主要体现在视听技术的内在负荷价值与外在应用价值两个方面。
首先,在复制主义资源开发观的影响下,开发主体忽视了视听技术内在负荷价值的彰显。哲学领域的技术负荷价值说认为,技术是人的目的的展现方式,目的的设定就负荷了人的价值[8]。学者吴国盛将这种“目的的展现方式”称之为“意向结构”。譬如,所有的锤子都指向它的砸功能,这里的“砸”就是锤子的意向结构。那么,视听技术的“意向结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应是“再现”。也就是说,视听技术指向的是“再现”功能。
细分地看,不同的再现技术实际上指向的是不同类型的再现功能。譬如照相技术,它指向的是静态且无声的再现功能;又如有声电影技术,它指向的是动态且有声的再现功能;至于今天的数字视听技术,它的“意向结构”应是一种丰富且多元的再现功能。在一个拿锤子的人眼里,世界就是个钉子;在手持相机的人眼中,世界就是一幅照片;而在掌握数字视听技术的人眼里,世界应当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再现方式。在这许许多多的方式中,理应有一类适于教育并能优化教育的再现方式。从学科使命上看,创制这类方式的任务无疑应由教育技术人来承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来看,我们显然并没有完成好这一任务。
其次,对于视听技术内在负荷价值的忽视,进一步导致了视听技术外在应用价值的消解。每一个将视听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其本意都是想利用视听技术促进与优化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不过,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本意。诚然,从资源的宏观效用看,在互联网时代,任何视听学习资源只要被上传至网络,其在扩大教育资源覆盖面、提升教育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必然有所裨益。然而,就资源的微观价值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必须承认的是,现实的教育世界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不优秀的教师,有不专心的学生,也有不完美的课堂。此时,倘若开发者们将复制主义开发观奉为圭臬,一方面,教育现实中的许多不足之处难以避免地被复制甚至放大;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用技术来促进人类学习”的学科使命[9]。
三、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的理论构想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现实之困,更在于发现走向美好世界的理想之路。在前文论述中,笔者无疑是以批判地态度指出了实践背后的复制主义异化倾向及其引发的种种现实之困,然而,假如我们仅仅停留于此,而不进一步尝试建构一种能够优化实践的新观念,那我们的批判便不能成为推动实践改善的有效力量。那么,有益且有效的建构究竟该向何处去?笔者以为,回归视听学习资源肇始之初的美育理念,建构一种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乃是一种可能的理想之路。
(一)感性教育: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的理念缘起
一般认为,视听学习资源萌生于感性教育理念的倡导。萌芽的种子首先可以追溯到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Amos Comenius)。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首位真正的先驱”[10],夸氏的感官教育思想被看作是视觉教学运动兴起的思想源头。此外,夸美纽斯曾绘制出一本被誉为“最杰出的教科书”——《图画中见到的世界》(Orbis Sensualium Pictus,亦译作《世界图解》),该书“以图画来表现和命名世界上主要事物及人的一生中的各类活动”[11]。在谈及该书影响时,有学者就指出,该书就是“‘视觉教育’早期的具体实践的范例”。与夸氏一脉相承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Heinrich Pestalozzi)“十分重视直观性教学原则”,他认为“直观是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因而也是一切教学的基础,如果没有直观教学,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周围事物的正确观念,不可能发展思维和语言”[12]。
事实已经表明,源自夸美纽斯与裴斯泰洛齐的感性教育理念对美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视听学习资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这点也已经为学界所公认。无论是从最初的教育幻灯片,到后来的教育电影;还是从早期的电教教材,到今日的教学视频,应当说,种种样态的视听学习资源背后蕴含的感性教育理念都是显而易见的。
而感性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美育理念。一方面,从词源上来看,感性教育与美育本就同根而生。美育在德语中原为“AsthetischeErziehung”,而“Asthetische”的词源是希腊文的“aisthesis”,意为感官(感觉)认识。此外,作为形容词的“Asthetische”,其名词形式“Asthetik”除了有“美学”的意思,还常常翻译为“感性学”。另一方面,在过往的理论生产中,二者也是相伴随行。譬如,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Alexander Baumgarten)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美学专著——《美学》。在该书中,鲍姆加通不仅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类感性认识的学科,而且指出“美学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又如,“康德(Immanuel Kant)一方面也把美界定为‘感性现象’,另一方面还在更接近希腊词源的原初意义上把美学界定为‘关于感性认识条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conditions of sensuou sperception’)”[13]。再如,我国美学家李泽厚曾有一个关键的命题———“建立新感性”,并且,他认为这必须倚重美育[14]。综上,无论是从概念的原本意涵来看,还是从学者的主观认知来看,感性教育都是美育的重要内涵之一。据此可以判断,开发视听学习资源乃是信息技术时代美育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因此,本文之所以提出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并非无中生有、主观臆测,而是倡导一种返璞归真式的回归。如此以来,需要进一步探寻的是,为何要寻求这种回归?这是一个关乎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是否合理的前提性问题,必须回答。
(二)学美与共: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的完满追求
为什么要回归肇始之初的感性教育理念?笔者以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一理念乃是契合前文提及的“用技术来促进人类学习”的学科使命的。作为体现感性教育理念的实践,开发视听学习资源最初的目的便在于为学生学习抽象的教学内容提供具体形象的感性认识,提高教学效果[15]。因而,本文所倡导的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学科使命的践行。
不过,由于感性教育是一种宏观性的美育思想,难以为开发视听学习资源提供具体的指引。因而,建构合理的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需要在感性教育的宏观指引下,继续从上游美育思想中寻求更为适用的理论工具。在笔者看来,源自学习美学的“审美学习论”值得借鉴。所谓审美学习,是指只有从根本上把学习过程变成审美过程,才能使学习带有愉悦而高效的统一性质,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6]。
以审美学习这一美育理念为指引,便意味着:理想的视听学习资源不仅要有优美的属性,还要促学的功能。这二者实际上指向了视听学习资源的两个判断维度。如果把“资源是否优美”作为一个维度,把“资源是否促学”作为另一个维度,便可以区分出四种视听学习资源。第一种是资源优美且也能促学;第二种是资源优美但不能促学;第三种是资源不优美但仍能促学;第四种是资源不优美且也不能促学。不用说,理想情形是第一种,这是视听学习资源开发实践的必然追求。而前文所述的复制主义的视听学习资源开发实践则常常导致第三、四种状况的发生。这里,笔者将上述第一种理想情形下的视听学习资源称之为“学美与共”的视听学习资源。所谓“学美与共”,指向的是视听学习资源的一种完满属性: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促学功能,并且,二者常常是相得益彰、相融共生的。
(三)寓学于美: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的实践途径
明晰了回归的方向之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这种回归究竟需要如何实施?期待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真正对当前及未来的实践有所裨益,就必须使其从理念层面向实践层面过渡,这就需要创生一种既契合理念意涵又符合实践要求的桥梁式的可行途径。本文认为,“寓学于美”应是这样一种桥梁式实践途径。
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所提出的“寓学于美”是对古希腊思想家昆图斯·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一种生发。贺拉斯说:“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7]其本意在于,教者应按照快乐的特点开展教育教学,这要求教育教学的方式不仅要有教育性,还要有愉悦性。同理,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寓学于美的要求在于:资源开发不仅要契合视听艺术的基本原则,而且要遵循教与学的基本规律。
仅就视听学习资源的构成元素来看,这种要求可以通过内外两个方面的创制来实现。首先是外在形式上的寓学于美,它是指开发者应尽量确保视听学习资源具有一种能够激起积极学习情感的外在形式之美。譬如,以动画的形式培育幼儿的亲切感;又如,以漫画的形式提升中小学生的积极性;再如,以电影的形式提升大学生的接受度。凡此种种都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激起学习者内在的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的积极情感。其次是内在结构上的寓学于美,它是指开发者应努力使得视听学习资源具有一种能够重构学习知识的内在结构之美。譬如,当视听学习资源在按照知识的逻辑平铺直叙地呈现而令人生厌时,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转述或重构知识或许更加有益且有效。除了“讲故事”,在视听学习资源中重构学习知识的方式还有其他很多种。不过,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一个必须的前提是促进学习品质的提升。
四、结语
在视听学习资源开发美育观的指引下,前文所述的种种影响与危机便有可能得到化解。如果我们实施的都是“寓学于美”的资源开发方式、创制出的都是“学美与共”的视听学习资源,那么,一切都会有所改观。机械的“实况录像”将变成一种穿梭于艺术与教育之间的复杂的创作活动;单调的“课堂搬家”将变成形象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视听作品。视听学习资源将成为“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学习法宝。
与之相应,唯技术指标的片面评价方式将不再合乎事实,对视听学习资源的评价至少需涉及技术性、艺术性和教育性三个维度;资源开发主体也将由单纯的技术操作者变成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其在教育领域的特殊地位自然不可替代;更重要的是,视听技术的内在价值便有可能得以充分彰显,更好地发挥其在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微学习资源开发与传播研究”(编号:CCA15015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吴文涛,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舒予,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现代远距离教育》2018年第1期
排版、插图来自公众号:MOOC(微信号:openonline)
喜欢我们就多一次点赞多一次分享吧~
有缘的人终会相聚,慕客君想了想,要是不分享出来,怕我们会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