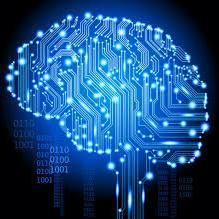美军的AI战略正开始类似于一款糟糕的约会应用:大量滑动匹配,却鲜有持久关系。特朗普政府的新版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展现出将事务推向新层次的潜力。该计划呼吁美国国防部深化对算法战的投资,要求将高级军事学院转变为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让学生学习并应用核心人工智能技能。此方法呼应了美《陆军转型倡议》中将人工智能智能体整合至下一代指挥与控制的号召。
实现特朗普政府算法战的愿景,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军事职业中高级教育的构成,并接纳关于创建数据驱动型学习组织的关键理念。
事实上,美高级军事学院应成为人工智能训练、研究与应用的中心,使教室更趋近于战斗实验室而非传统讲堂。专业军事教育应充当有机优化生态系统——即总参谋部的现代版本——在此系统中,学员与教职人员的问题解决过程被捕获并反馈至人工智能系统。
教学应减少对历史与理论的泛泛而谈,更聚焦于解决紧迫的作战问题,并将最优学员解决方案作为有机反馈回路,通过人类反馈为现代职业构建强化学习。这些院校应变得更精简、更精英化,减少行政人员与教职数量,并让教师兼具战争应用研究职能,确保教室本身成为新知识创造与完善的场所。
若实施得当,这些院校才能真正成为军队的"新大脑"。
美国防部人工智能现状
生成式人工智能转型在美国军方仍是一个尚未整合的开放市场。ChatGPT、Llama、Gemini和Claude等基础模型,以及Palantir的"梅文"、Scale AI的"多诺万"等应用,都自诩为规划与决策的未来之路。在真实进展旁,充斥着为展示而打磨却缺乏实质的产品。黑客马拉松、"雷霆锻造"等实验以及无穷尽的"军用GPT",模糊了创新与幻象的界限,令领导与参谋军官难以区分实用性与炒作。
这场喧嚣分散了构建人工智能所需智力基础的艰巨任务。人人自称人工智能专家,却鲜有人真正掌握底层技术以应用于战争。随着行业、教师与同行不断提出拙劣主张,盲目相信炒作的概率与日俱增。学员离开时带着不切实际的期望或变得麻木,宁愿回避而非投身于构建自身人工智能智能体与特定用例应用。
当前缺乏的是将历史、理论与条令精心组织成机器可学习形式的系统性努力。若无此策展基础,模型将继续更了解名人而非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或威廉·斯利姆。军事专业人员迷失于喧嚣之中。
若军方严肃对待人工智能,就应优先考虑专业知识而非表面表现。真正的挑战在于策展领域特定知识,使算法能应对战争中的迷雾、摩擦与动态目标,并应用作战设计、重心等概念以及脉冲作战与马赛克战争等新兴理念。
构建军官团的大脑
在智能体人工智能时代,军队需要一个集体智慧体系,使军官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挑战算法产生的结论。专业论坛应当成为学习与新知识创造同步进行的场所,这些知识将直接输入用于规划与作战的系统。构建这一"大脑"不能外包完成,因为它依赖于捕捉军队最优秀思想家处理问题的方法,并运用这些见解来优化基础模型。
军队的这一"大脑"是总参谋部这一传统概念的延伸,但已适应现代信息网络。19世纪末,斯宾塞·威尔金森出版《军队的大脑》一书,描述了德国总参谋部及其在规划成功军事行动中的关键作用。普鲁士模式凭借其关于教育及如何培养"具有远见的军人"的独特理念,成为军事组织的标准范式。该模式特别重视通过历史案例和决策推演进行战役分析,这一思想体现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五章关于批判性分析的论述中。真正的职业军人运用历史积累对战争复杂性的洞察,同时以应用于未来战役的视角展开研究。战争研究与作战规划由此成为相互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要求减少讲座和漫谈式研讨会,增加设计与实施战役的时间。这意味着文职教员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学习联合全域作战及规划方法,而不是固守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
如果实施得当,这一过程将产生新知识。学员不仅要证明自己能解决陈旧的"学院式"方案,更应展示其作为思考主体——军队大脑中神经元——的能力,能够进行评估判断、分析行动方案并进行功能性规划。这一分析过程既锤炼他们的判断力,又为解决关键作战问题提供选项,同时确定未来部队建设需求,包括战区态势、准入权、基地使用与飞越权等执行计划的关键要素。
为使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发挥作用,这种知识生产过程应成为现代职业军事教育与高级军种学院的核心动力。教员应与学员共同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传授笼统的概论和见解。学员应接受高强度训练(其中有些人会失败),以证明他们具备专业基础知识并能将其应用于重大战役研究。
最重要的是,分析过程——从周密规划到战役分析与兵棋推演——应基于条令与特定领域数据集,军队可利用这些来优化人工智能模型。基础模型本质上是通用型的,因此需要优化改进。在最基本层面,这意味着提出更精准的问题,引导算法寻找答案的方式,并设定规则以约束其输出。然而现代战争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基础工作,它要求采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使课堂创造的知识用于优化支撑全军人工智能系统的模型。
这意味着教室将成为数据采集场所。职业军事教育成为一种新型"军队大脑",算法在此向顶尖思想家学习。这一转变并不困难或昂贵,但确实需要结构性和文化性变革。
在结构上,军事院校可能会变得更精简但更精英化。通过减少行政支持人员和教职员工节省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人工智能许可和在教室建立数据采集系统以训练算法。这将需要修改联合条例,这些条例导致学校淡化对现代战争的关注,同时更好地协调研究生学位和学员学习成果。
在文化上,教员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现代职业军事教育中有优秀的教授,他们仍将有一席之地,但这将是一个他们既从事教学又与学员共同研究、并专注于战争而非个人项目的职位。这将是一个更注重实践而非核心课程的环境,接纳合作教育和联通主义作为学习理论。学员通过实践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知识,用于优化作战部队中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和系统。这也将是一个教员——根据定义——应作为顶尖研究者的环境,他们与学员团队共同解决关键作战问题。
拥有新的"军队大脑"
军事教育是一门需要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古老艺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现实。教室应成为作战实验室,团队在此分析问题、检验假设并为作战问题生成新的解决方案。整个过程成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核心,从而为算法时代有效创建一个新的"军队大脑"。这是一项大胆的改革,需要从教员和学员评估方式到技术在课堂中的作用等实质性变革。这些变革更多取决于审慎的选择和对当前职业军事教育设计与执行中机会成本的思考,而非资金投入。行政教职(如院长和学术支持人员)将减少,而对课堂教学与实践结合的要求将提高。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机制来识别关键作战问题,超越简单清单和技术性数据采集与模型优化方法。
历史上最优秀的军队都善于反思和创新。他们不沉溺于过往荣誉,而是培养能够把握时代的"具有远见的军人"。在21世纪,这意味着将人类最佳判断与人工智能系统相结合,以创造规划与作战的新方式。这一进程应从军事院校开始。
参考来源:warontherocks